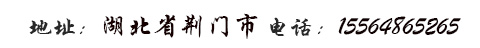藏书印与版本鉴定
|
中科医院专家 http://hunan.ifeng.com/a/20170705/5797804_0.shtml ?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 玺 印 玺印 玺印和符节一样,最早是用做取信的标识。从何时起,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,作为收藏、校读、鉴赏等等的印记,不可确知。唐王建《宫词百首》中有:“集贤殿里图书满,点勘头边御印同,真迹进来依数字,别出锁在玉函中。”王建是唐代宗大历十年(年)进士,初为渭南尉,历秘书丞、侍御史,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。其《宫词》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。可见藏书用印,早在雕版印书之前。 盖印习尚 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,以明清两代为最盛。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,差不多都有几方,甚至几十方,各种形制,不同印文的印章。这些藏书家,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。他们学有专长,精于鉴别。因此,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、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,很受目录学家、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。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,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。 印章样式 印章和版式、行格、字体、纸张、墨色、讳字、刻工、序跋、牌记等等一样,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,但是又有不同。版式、行格等条件是先天的,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,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。印章则是后天的,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,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。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,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流传源流。这一点,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,也是很重要的。书商射利,伪造版本,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。就印章本身来说,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印文作为史料,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异名别号、生年行第、氏族乡里籍贯、家世门第、仕途经历、学行师承、癖好志趣等,也可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、玺印制度和谊里关系。关于这一方面,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。 图书用印 图书用印,源远流长,但以明清两代为盛,大概与宋元以降,文人喜欢治印,明代文(三桥)何(雪渔)而后,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。明清两代的藏书印,不但数量众多,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。特别是清人印,从风格上看,有凝重的浙派印,有秀逸的皖派印,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,而独树一帜的名家作品,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,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。印章的形制和印文的内容,明清两代也都有新的发展。 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,钤盖上几方朱白得宜的藏书印,朱墨灿然,古色古香,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,使它成为艺术珍品。这大概是历代藏书家,喜欢在藏书上用印的又一个原因。 名号印 印文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,分为名号印与别号印。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;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。如“季振宜印”、“沧苇”;“钱曾之印”、“遵王”;“乾学之印”、“健庵”等。明代以前多用单印,或刻姓名,或刻字号。清以后多用双印,一颗印刻姓名,一颗印刻字号。两颗印大小一致,文或俱白或俱朱,或一白一朱,名上号下,钤盖在一本书上。也有单刻一个姓的,如赵松雪有“赵”字方圆二印,缪荃孙有八分书朱方“缪”字印。或者把姓名字号全部刻入一印,如“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”、“王禹声遵考甫一名卓字昭回”、“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”等。像“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”、“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一”两印,或冠以籍贯,或缀以行第,但以姓名字号为主,仍属名号印。名号印中,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联珠印,是把姓名拆开,每个字自成一方,几颗印连缀钤盖,姓名方才完整。顾蒙、孔继涵等,都有这种印。 我国古代文人,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,起上一个别号,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,并用以入印,这种印叫别号印。如赵松雪的印“水晶宫道人”,文彭的印“渔洋子”,唐寅的印“六如居士”,阮元的印“研经老人”,*丕烈的印“佞宋主人”等。 堂号印 堂号印:我国古代文人,还习尚于把个人起居、游憩、读书、藏书等处所,据其特点题上一个堂号并用以入印,这种印叫堂号印,也有人叫做斋馆印。如文征明的印“停云馆”、“辛夷馆”、“悟言室”、“玉兰堂”、“翠竹斋”、“梅华屋”、“梅溪精舍”;项元汴的印“天籁阁”、“退密斋”、“世美堂”、“世济美堂”;毛晋的印“汲古阁”、“目耕楼”、“弦歌草堂”;丁丙的印“善本书室”、“八千卷楼”;杨以增的印“海源阁”、“宋存室”、“四经四史之斋”;瞿镛的印“铁琴铜剑楼”;张金吾的印“爱日精庐”;*丕烈的印“百宋一廛”、“士礼居”、“陶陶室”、“读未见书斋”、“学耕堂”等等。 以上举例,是印文比较简单的。有一些名号印或堂号印,或者在名号前冠以籍贯、乡里、氏族、官职,或者在名号下缀以“珍藏”、“秘籍”、“收藏印”、“书画印”等尾词,如“浙右项笃寿子长藏书”、“长白敷槎氏堇斋昌令图书”、“汪士钟字春霞号朗园书画印”、“当湖小重山馆胡氏遽江珍藏”、“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元习之记”、“古槜李江山风月主人子渊项元深氏世济美堂收集书籍印”,以及“八千卷楼珍藏善本”、“桐凤庼所收清儒著注选戢校刻书印”、“曾在南云蔡氏犹半轩群签之内”等,文字虽然多所变化,但以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堂号为主体,仍属名号印或堂号印。 由于藏书人的境况不同,堂号印多少不一。如文征明有不同称号的堂号印十颗,项子京六颗,毛晋、*丕烈各七颗,上面提到的几颗,是善本书上常见的。堂号印和前面提到的名号印,是藏书印中使用最多,最常见的一种。 我国古代文人,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,起上一个别号,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,并用以入印,这种印叫别号印。如赵松雪的印“水晶宫道人”,文彭的印“渔洋子”,唐寅的印“六如居士”,阮元的印“研经老人”,*丕烈的印“佞宋主人”等。 鉴别印 这种印多见于宋元刻本书,用者多数是精于鉴别的名家,印文用语以简单肯定的居多。如“沅叔审定”(傅增湘)、“艺风审定”(缪荃孙)、“芙川鉴定”(张蓉镜)、“杨绍和鉴定”、“叶名琛名澧兄弟同鉴定”、“苏斋真鉴”(翁方纲)、“完彦景贤精鉴”,以及“高氏鉴定宋刻版本”(高濂)、“贵阳陈氏审定宋本”(陈渠);“毛晋秘箧审定真迹”、“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印”、“长白马佳氏宝康审定宋元旧椠并元明旧抄旧校之记”等。当然,印文也有含蓄一些的,如“谭元庆学看元本书籍印”。 有些名藏书家,如项元汴、毛晋、季振宜、席鉴、杨守敬等人,更在所藏善本书上,加钤“宋本”、“元本”、“赵宋本”、“甲”、“乙”或“神品”、“稀世之珍”、“天下无双”、“ 孤本”等圆方小印,以为版本品位高低的标识,这种品评性质的印章,也属于鉴别印的范围。 校读印 这是对善本书上常见的校勘印与阅读印的通称。校勘印如“益之手校”(杨以增)、“喜孙校本”(汪喜荀)、“惠定宇手定本”(惠栋)、“又玄斋校阅过”(秦四麟)、“曾经燕庭勘读”(刘喜海),以及“张海鹏校正图书记”、“南陵徐海昌勘误鉴真记”、“颖川陈氏校定典籍之章”(陈子龙)等。阅读印如“彭兆荪读”、“深柳读书”(金元功)、“赵凡夫读残书”(赵宦光)、“曾经筠川读”(刘筠川)、“吴岫尘外轩读一过”,以及查岐昌的印“巢经阁读古记”、吴翌凤的印“枚庵流览所及”、“丁福保三十以后读书记”等。 从上面的印文看,校勘印和阅读印似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印章,但实际上校读相因,二者往往不能截然分开。 钱谷的印“白发抄书”和“钱谷手抄”,沈与文的印“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雠记”等,也可归人校读印一类。钞书与刻书,也不能和校完全分开。明清两代很多的藏书家,也是钞校名家和刻书家。 校勘印和钞书印,多用于钞本和批校本,在刻本书中也往往见到。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huanshegana.com/csgsltx/1109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种植射干苗期如何管理
- 下一篇文章: 诗词鉴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