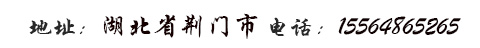红豆
|
北京看皮肤科好的医院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yqyy/160214/4770025.html 红 豆 那年夏初,我在小城拍纪录片的素材,遇见了一个姑娘。 小城我去了多次,只是那位姑娘,我头一次见。 那天夜里,云色浓厚,朦朦地遮了月亮。我从住处下山,带着相机,捕捉小城的夜。 在小城呆久了,哪怕是在漆黑的夜晚独走山路,也只觉如履平地。高脚楼、玉米地、青青的石板路,皆被我记录在胶卷里。 小城的夜色,几家灯火,暗影婆娑。只有城西一街商铺林立。旅人踏着青石板,一簇一簇疏疏地散步,灯火通明。一路上虫鸣清响,我随手拍了几张树影清泉,不甚满意。 我拎着相机,转过几座高脚楼,穿过一条小街,突觉前方不远处的巷口里,浮出一簇黑影。夜如水色,月光晦暗,仅凭遥望,我只能看清那影子的轮廓,像个姑娘。 那影悉悉卒卒地提了什么,直向前走着。我好奇心突发,缓缓跟在后面。 月从云里出来了,月光如雨,明明如镜。那是个姑娘,提了一桶花,正不疾不徐地走着。 我不知跟了几许,只觉虫鸣渐渐消弱,云又厚起来,不远处一片灯光明亮,有人声鼎沸。 那姑娘路很熟的样子,虽提着一桶花,却也不累,三转两拐,便到了街口。 姑娘似是来卖花的——我骤然停住脚步,隐在阴影里,看她往哪里驻脚。小城多花,这样的花贩立遍街头巷尾,见多不怪。 那姑娘在街口停了一下,顺着人流,走进街去。 街灯的光*澄澄地落在她身上,落在那桶花上,忽明忽暗。她走在石板路的中央,走过临街一家一家店铺,旅人从她身侧擦过。 原来这姑娘是个流动花铺:我穿过一簇一簇的旅人,想赶上她,买朵花插在住处。正要抬腿,清清泠泠的声音从街心传来。 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”有人在诵诗。 我讶异地抬头张望,姑娘的身形穿过层层叠叠的旅人,忽明忽暗地映入我的眼底。再看她提的那桶花,可不是一桶新鲜的红豆枝子,红艳艳的缀满枝头。 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清脆疏朗的声音,宛若微风轻抚挂铃。姑娘的声音叩击石板路,穿过一众的叫卖声和嬉闹声,像一颗石子投进潭水,泛起重叠涟漪。 街上行人纷扰,有人侧目,有人指指点点。姑娘不疾不徐地行在街上,提着桶,诵《红豆》,像水畔踱步的白鹭鸟。偶尔几个买花,她便停下来,付了钱,挑一只,她再继续走。 我愣愣地望了片刻,被人流裹挟着,不由自主地往前挪步。周遭的人声,眼前的灯火,皆幻成一团一团虚影,擦过身侧。走了一阵,身边的行人渐渐稀疏,大概是快到街尾了。姑娘的身形在我眼中涂上一层薄薄的夜色,我犹豫了一下,放缓脚步。 在夜色与灯色的交界,商铺黑漆漆地立着,石板路青影黝黝。街外,原野开阔,草木朦胧,群山的影子,逼狭地伸向天空。姑娘的身影在茫茫夜色中显得模糊而渺小。 我目送姑娘出街,心里一阵怅然。方要离开,发觉路边上有一颗“小石子”。我弯下腰,从一团草叶里拾起它——是一颗红豆,新鲜的红豆,暗红色的,在夜色的衬托下,几乎要融进我的手心里。我猛地抬头。 姑娘已然走远。卖花者众,却哪一个也不是姑娘的身影。我感到一阵茫然若失,怔怔地立在街尾。我的眼睛追随姑娘的身形:姑娘走出街,渐渐地消失在夜色里了。 清晨的商业街睡眼惺忪,全无昨夜那欢声笑语的模样。商铺暗淡无光,石板路黑漆漆的,远望像浮着一层油光。旅人散去时,商业街总显得冷清。微风拂过,小铺上支立的酒旗象征性地摆了摆腰肢,又顷刻塌软了。 我举起相机,记录下清晨的商业街,像窥破了别人的秘事,心里猛地抽动了一下。我急忙离开了。 熟悉的街道,熟悉的拐角,熟悉的小铺,昨夜的情景历历在目,只是不知道那姑娘 在何处落了脚。然而昨夜我本无意赶上那姑娘,只是那婉转的声音缠绕在耳际久久不得消散。我想了再想,小城再小,花店也有七家,一家一家地挨着寻,总感觉做贼心虚。况且,若这姑娘原不是小城的人,只是偶尔来小城卖几朵花——我眺望着远山脚下星点村落,心里笑自己异想天开。 片子还差几个镜头,计划是拍些人物肖像,展现小城的人文风光。趁早晨光熹微,我在街上游荡,不期走进一条小巷。 炊烟轻轻袅袅地飘出窗外,渐渐飘散在暖融融的空气里,与那未及散尽的晨雾融为一体。不知谁家的狗高声地叫,一排鸭子列队穿街而过,摇摇摆摆地好像巡逻。屋檐下,一个姑娘穿着蓝布衫,提一柄小喷壶,站着浇花。我拉近相机的焦距——姑娘身旁,各色鲜花开得淡妆浓抹,争奇斗艳。昨夜那姑娘卖花的情景涌上我心头,我盯着相机屏幕上的花店外景,决意前去打听一番。 这家花店,我早听说了,是一对母女开的。开在半山,小城的边上,一条僻静的巷子里。我在小城逗留了这么久,竟从没拜访过。我踌躇了一下,收起相机,穿过马路。 姑娘浇了花,端了一把凳子,坐在屋外剪枝。我整整衣冠,敲了敲门廊前面的柱子。 “买花吗?”姑娘停下手中活儿,抬头看着我。 “这玫瑰真好看。”我指了指她面前那一桶花,是新鲜的红玫瑰。 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笑了一下,“好看确实好看,只是有刺。” 我没接话。 姑娘亮了一下她的食指,指肚上有一道深红色的伤口。“它扎的。” “哦!”我停顿了一下,想安慰姑娘,她却接着说,“玫瑰要剪刺。你看,像这样,把它的刺斜着剪下来”。她从桶里拿出来一枝,用剪刀比划了一下。 “给玫瑰剪刺,就好比给人剪指甲。你想,你要去握别人的手,却被长指甲扎了一下,心里是什么滋味?” “嗬!”我也笑了,蹲下来看她修剪玫瑰。 她手法纯熟,剪刀利落,手起刀落间,明艳的红玫瑰尽褪尖针。 阳光一点一点明亮起来,斜穿门廊,映得花店一团暖棕。乱花与蜂蝶的影风姿潇洒地印在老墙上,上演着一出没有剧本的皮影戏。我打开相机,拍摄姑娘翻飞灵动的手。 姑娘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。 “拍纪录片的。只拍手,不拍人,看你剪花剪得漂亮。”我笑道。 她也笑笑,“倒也没什么。只怕放出来,给学生看笑话。” 姑娘说她做老师,在小学教语文。那花店是她母亲开的。她闲暇时间,常来帮忙。 “听你这口音,不像是本地啊。”我好奇地追问。 “是啊,我不是本地人。”她插好一支玫瑰,抬头看我。“怎么,只有小城的人,才能开小城花店?”她眨眨眼睛,反问道。 见我没说话,她反倒笑了,探身从另一边的瓶子里抽出一把满天星,塞进我怀里:“给你的,拿回去插在瓶里,好养活——我给学生也送花,全当做奖励。” 我抱着一捧花,一时语塞。满天星的香细细柔柔,盈满怀中。 “对了,我才记起来——”我猛然想起那枚红豆,“你昨晚,在街上落了颗红豆。” 我掏出那枚红豆。她一愣,慢慢放下剪刀,半晌没有说话。 “我昨晚在街上,看到你卖花,本想买一束的。”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,心一横,便把胳膊伸到姑娘面前。 暖风拂过,吹来满屋花香。阳光仿佛透明的,轻盈地飘落在姑娘肩头。那枚红豆躺在我的手心里,明艳光泽,是微微润湿的红。姑娘慢慢地拿过它,静默了许久,或许是有很多话想问我, 却什么也没说,找到了一张软软的皱纸,把红豆包了起来。 红豆——相思子,三月开花,九月结果,纤枝窈窕,翠叶朦胧,是姑娘 的花。鲜亮的红豆子凝在枝头,那是有情人无言又无缘的泪珠。相思豆结了果,便剪下枝子,或摘了果子——枝子插在瓶里作装饰,果子晒干,串起来做手链。那些绿条条的枝子,被风裁得乱中有序。叶子挤挤挨挨的,浓墨重彩,衬得顶上那红珠子愈加明艳清高。那红豆子,就像上世纪遗留下的泪滴形耳坠,是压在箱子底下的旧情物。多年以后重新戴上,镜中少女变成了太太,耳坠依旧在镜中闪烁反光,可那皱纹岂是三两杯薄酒就能消去了的,再多的唏嘘,也只能感慨物是人非旧情难言。 有次我问姑娘,为什么喜欢相思豆,是不是寄托了某种情愫。她没答话,转身进屋,端出两杯水。“喜欢相思豆,一定为了某种情吗?”姑娘反问我。“难道喜欢必要有因,难道爱花必是因情——就好像,玫瑰只能象征爱情,这是毫无道理的。红豆的相思之意,难道不是人们赋予的。” 姑娘说话的时候,手里拨弄着一束红豆枝子,凭栏远眺。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,亭宅楼院,皆是村庄的模样。 姑娘从没和人恋爱过。但我猜想,在她心中大概是有一种情愫,像是爱情,但更像是一种期许,一种虔诚忠实的感情。她对待这种感情,宛如信徒对待他们的天父。这种感情不因任何人而起,不因任何人而终,漂荡在天地之间,实在无处安放,就寄托在红艳艳的花上。 我听说她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小城。她的母亲身体不好,像是生了什么病,整日呆在屋子里。我猜想她放弃了考研的机会,来小城做老师,是为了母亲的身体。我多次想询问她,却碍于情面,一直没能问出口。 对于做老师之前的人生,姑娘总是隐晦不表,偶尔说起,就蜻蜓点水地谈上一两个字。而每当提起学生,姑娘无奈地摇摇头,嘴角却总噙着笑意。她谈班级趣闻,谈她如何与学生斗智斗勇,如何用花朵拉近学生的心,给他们讲梦想,讲远方。每当这时,姑娘的眼神总是闪烁着,淡淡的神情仿佛也有光。 自从结识了姑娘,我便常来花店帮忙,街上也不常去了。她教我怎么剪枝,怎么插花,怎么照顾些花花草草。有时候我举着相机拍她,拍她梳辫子,拍她把菊花插在头上,拍她穿着蓝布褂子,拍她逗弄门前小憩的懒猫。店里人不多,我把相机架在桌上,拍内景,从清晨拍到傍晚。她再没有走街串巷地卖花了。 有天晚上她留我吃饭,说我那段时间里表现好,她为我庆功。我一愣,笑着跟她说:“我来帮忙,却不见得把生意帮衬得多么好。”姑娘把一盆云竹搬进屋,斜着眼看我,笑道:“你这人俗得很,生意是生意,朋友归朋友。再说,给两个人做饭是做饭,给三个人做饭,也是一样做。” 她总像对待她学生那样对待我。 我语塞。我本不想麻烦她做饭,却又没有理由拒绝主人的邀请,只好默默无语地走出去,把剩下几盆盆景搬进屋。 姑娘炒了几盘青菜,又炖了只鸡。老旧的厨房里烟斜雾横,香气却飘散得很远。她麻利地炒菜,不时用手背抹一把眼泪。姑娘不让我帮忙,甚至连厨房也不让我进。我只好倚在门框上,偏头看着她在一团烟火里忙碌,她还不时地咳嗽几声。 饭好了,姑娘在客厅撑起桌子,端上饭菜,扶她母亲出来。我插不上手,只能在旁边慌慌地站着。她很快布置停当,招呼我吃饭,又端上一瓶米酒。 那晚我们聊得很畅快。我向母女俩讲述曾经拍纪录片时的奇历,我和村民们聊家常,与群狗赛跑,又一连一个星期把相机架在旷野,只为拍一次*昏里的落霞。我手舞足蹈地比划,说得眉飞色舞。姑娘笑倒在桌上,她母亲微笑地看着她,眉头却微微地皱了起来。 姑娘的母亲让姑娘敬酒,问我对小城的印象如何。我瞥了一眼姑娘好奇的眼神,沉吟了一下,往日走街串巷的回忆一幕一幕闪过脑海。 “小城多花,小城人爱花。”我缓缓开口。 姑娘的母亲笑了一下,微微点头。我继续道。 “就面积而言,小城真的很小,小到只有一所小学,一所初中;一家诊所兼着药铺,还摇摇欲坠地建在半山上;六家饭馆,可花店却有七家。这足以说明,小城是一座花的城。” “对,对,一点儿没错。”姑娘连声附和,又笑得花枝乱颤,笑声像扑簌簌地从树枝上惊落千层雪。 我受了姑娘的赞同,心里大为欢喜,隔着桌子冲姑娘一笑,继续道。 “凡是来过小城的,无人不知小城爱花。小城的人,一年四季都爱摆弄鲜花,还把花儿插在门头上——刚来小城的时候,我还有些不适应,怕招虫子。” 姑娘没有接话,我暗觉这话有些不妥,急忙补充道,“就是因为爱花,小城里卖花的小铺也不少,但只有姑娘的花铺会诵诗。还有姑娘家的红豆,堪当小城一绝。” “瞧你这张嘴。”姑娘不住地摇头,又忍不住露出笑颜,“要真像你说的,那我家花店岂不是要被踏破门槛?” 我也自觉话说得越来越没谱,脸一红,赶忙低下头夹菜,却不觉自己面红耳赤的模样已被姑娘的母亲看了去。 “说起小城,也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。我年轻的时候,也算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却再没有找到一处比小城还养人的地方了。”姑娘的母亲缓缓说道。 “阿姨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 姑娘的母亲摇了摇头,没再说话。我却忍不住想像多年以后,姑娘白发苍苍,闲坐在摇椅上打瞌睡的样子:皱纹像涟漪一样地晕开,摇椅安详地咯吱作响,不知那时的姑娘,是否还会想起这个遥远的时刻。 “小城还是太小了。”姑娘接着母亲的话,感慨道。“连一所高中也没有。孩子们要想上学,还得跑 十里的山路,到隔壁县城去。” “不,不要紧!再过十年——不,五年!再过五年,凭我拍的片子,我保证让小城建一所高中!”我拍着胸脯说道。三杯两盏米酒下肚,我只觉得唇齿香甜,眼花耳热,遂发如此豪言壮语。 “那好啊,如此我便感激不尽了。”姑娘亦举杯,笑眼盈盈地望着我。我豪气干云地一饮而尽。 “天不早了,要我说就该休息了。”姑娘起身说道。我急忙跟着站起来。姑娘把母亲扶进屋,回身往走廊上煎草药。 走廊里灯色昏暗,小虫绕灯飞舞。走廊的那头黑漆漆一片,这头尚有些月光照耀,桌椅门廊朦胧入眼,是一片混沌的暗光。 小火炉烧得旺起来了,渐渐地,清苦的药香如丝如缕,和着晚风送入鼻腔。姑娘煎药的动作也行云流水,像我曾经观摩过的,那些书法大师们挥毫泼墨。我不由得挨得近了些,渐渐又闻到一股酒香。 “这是煎的药酒。”姑娘解释道。 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——我正好给学生讲到这一课,只可惜现在天气还暖。”姑娘搅了搅酒炉,一股热腾腾的酒气扑面而来。 酒香四溢,姑娘的发丝散落下来,脸颊被热气蒸得通红,好像欲滴的芍药花。“小城不下雪。”我呆呆地说。 晚风醉人,连空气都弥漫着一股酒香。门廊下,灯光昏暗,姑娘面色微红,闲懒地倚着老屋。我向她道别,只看了一眼她酒一般流盼的眼波,便一下子忘了神。我往前踏一步,踏进夜色里,脚步虚浮,一晃三摇,好像烈风中东倒西歪的芦苇。天地翻转,我跌跌撞撞地走在天上,走在银河里,好像在银河上行船。水波上下翻涌,月色星色好像剪碎的绸缎,一把撒进河里,蝴蝶一般飘飘漾漾,明晃晃地抓弄人心。清风送来远香,像光洁的蚕丝,一丝一缕缠绕身周。我化成了一滩水,一滴寒露,蛰伏在花瓣上,却又浑身颤动不已,忍不住淌进溪水里,随溪水奔踏欢歌,千回百转。我趴在地板上,四下一片我的呼吸,像漂浮着的海岛,忐忐忑忑,起起伏伏。虫声渺远,如一川瀑布。 我睁着眼睛躺在地板上,木地板咯吱作响,是有人走过的脚步声。 晨光明晃晃地照着。鸟声替了虫声,继续做这声的瀑布。透过窗子,我看到不知谁家的烟火缓缓升起来了,又被风吹散,好像一帆飘扬的烟的旗帜。哪家的鸡鸣三声,宣告新的一天天下一白。我忍不住想起那天姑娘给我讲“风雨潇潇,鸡鸣胶胶”:主人公的君子已经归来,可我却要即刻远行。我安静地躺着,一只雄蜂飘进窗子,盘旋一周,又盘旋地绕出去。我和姑娘很默契,谁也没先提起那天下午的别离。 曾经我多次来到小城,来了又走,挥一挥衣袖,只带走几段录像,留下几张录影。小城的样貌,好像已经印在我心里了,每一次来,并未觉得小城较前日有多少不同。小城好像一个年岁已久的老人,再多添几条皱纹也不会影响他的样貌。可是,那是曾经的小城,而我并没有遇见姑娘。我是小城的过客也好,见证也好,这样的异乡,我终是要离开。 我举起相机,抓紧时间记录这个已经不一样了的小城。半山腰上,炊烟缓缓升起。老农牵牛,在羊肠古道上踱步。水畔蚊虫纷扰。柳枝茂盛,仿佛绿意盎然的瀑布,泻进小溪里,染绿一溪碧水。 姑娘在学校上课。我在大街上闲逛,搪塞时间。日头浮涨,尘土飞扬。街上有人用柳条和杂色的野花编织花环。我想买一个带走,拿起来又放下,想了又想,还是把它记录在了相机里。一群女孩子一起卖红豆枝子,摇着小拨浪鼓,枝子有些灰头土脸的。我知道那些人不是姑娘,却还是挨个儿抱着期待望过去,又悻悻地缩回目光。 那是我 一次来小城。当时的我就深深地明晰这一点。 小城的春夏秋冬,我都曾经历过。我对小城的布局如数家珍。小城的溪流如长发,如白练,镶着珍珠,泻进潭中,宛若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城里常飘着花与木头的清香。到了深秋,浓厚的腊肉香更是从家家户户的木漆窗里飞出来,走街串巷地跑上一通,于是小城便笼上一层过冬的暖意了。也许现在,还要加上药酒的清苦香气,绵绵密密,浓醇饱满。也许小城冬天也会下雪了,这样姑娘就能在“晚来天欲雪”的时候煮酒细品,在落雪的天气里,给学生们讲北国的雪、南国的雪。 我这样想着,徜徉在小城的街道上,随手拂过小城的老墙、支立着老屋的木樑。天空蓝得清澈安详,早归的燕子已经三三两两地落在电线上,待要修补去年的巢。屋里的老妇人,聚在一起闲聊,一起绣花、纳鞋垫子,阳光斜斜地从窗户射进屋。也许姑娘会在这样的屋子里老去,陪着小城的山,小城的水,小城的孩子们。也许姑娘也会离开,就像那离巢的燕子——不,姑娘已经离巢了,已经飞到了小城,在小城里安定地筑巢。 姑娘不会离开小城。我坚定地想,坚定地相信姑娘,她会守着这座山,守着这些花,守着这群孩子们。 天色渐晚,空气冷下来。太阳醉了,迷迷糊糊地寻找住所。暮色从窗户里流进来,爬上窗边的蔷薇花。姑娘对着镜子,低着头,神情隐藏在暮色里。我站在姑娘身后,看着她耸起的肩膀,和镜中不知悲喜的倒影,久久无言。微风吹皱窗帘,窗帘飘起来,像吹鼓的风帆。我猛地冲过去,想要抓起姑娘的手,姑娘却突然转身,手心里捧着一串手链。 “你给我的相思豆,我做了手链。”姑娘低低地说。我一怔。 “我给你带上吧,路途遥远,至少保个平安。”姑娘柔声说道。我伸出胳膊。细线轻柔地缠上我的手腕,那颗红豆子缠绵地贴上我的皮肤,还残留着姑娘温热的体温。姑娘的手指从我的手腕上滑下来。 夜气从地板涌上来,幽暗潮湿,拉扯我的脚踝。我直直地盯着姑娘的脸,姑娘轻笑,目光澄澈柔和,宛若那夕阳的光。“来日方长,有缘自再相会。”姑娘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我看到姑娘的嘴唇开开合合,清泠泠的声音好像一丛荆棘,尖厉的刺一道一道地划破我的皮肤。我把目光从姑娘昏*的脸庞上移开,攥紧那枚红豆,扭过头去,大踏步地离开了那座老房子。姑娘在身后喊道:“相思豆有*,只是别吃了!”我没有回头,把那一道清婉柔美的身形抛给身后的夕阳,投进那群山和原野的阴影中去了。 从那以后,我再没有见过姑娘。那道身影在记忆里渐渐消散成沙,只留下那枚红色的相思豆,历经无数风雨的洗礼,却反而愈加鲜红欲滴。后来,那颗红豆子也渐渐变得松脆,好像轻轻一捏,就会散成粉末。那红色沉淀了下去,变得暗哑无光。那沉淀的不仅是当年夏月,还有后来流淌不息的年年岁岁。 (全文终) by复活REnaissance 愈青团 万物生长我们在寻找光亮 小红书同名搜索 盖一间温暖的房子 联系晾晾 在线投稿 点分享还是在看呢? 不然都点一下?!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huanshegana.com/csgxgls/1092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九川荐读董明珠六种人干不成大事,十种
- 下一篇文章: 中药二常考功效汇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