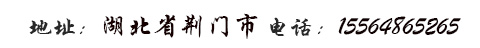大明王朝海瑞是被逼出山不,2个隐藏的细节
|
文丨卿心君悦 导语: 御前“三路诸侯”齐聚的会议后,因严嵩犯下两个错误(详情可见之前的文章),嘉靖继续默许清流与严党的斗争。 为尽快推行“改稻为桑”,严世蕃特选高翰文为杭州知府;而清流在裕王的敲打下,暗自推进“倒严”的同时,也不得不兼顾浙江的灾民。 于此,为让受灾的百姓少吃些苦,谭纶举荐海瑞为淳安知县;经谭纶“背书”介绍,海瑞得到了裕王和张居正的认可,但随后谭纶提出了一大难题: 海瑞无法跨越一个“孝”字,所以很可能不会出山。 对此,张居正则不以为然,大笔一挥慷慨激昂写了一封信——信中有“忠孝仁义”绑架的“硬”,也有满天“画饼”的“软”。 众人见此信,皆认为海瑞势必会“移孝作忠”。 果然,海瑞见到这封信和吏部的文书后答应出山,然而,海瑞此举,却非被迫,而是早有预谋…… 海瑞母子对话——显端倪一收到信与文书,海瑞未得海母的同意,便先行叫海妻准备路上吃的“荷叶米粑”。 此举尚可说海瑞“知母莫若子”,猜测到了海母即便满心不愿,最终也会同意其赴任知县。 可海瑞至少该表现出些犹豫与为难吧? 然而海瑞却没有。 若按谭纶的说法,海瑞早已一颗红心化作“孝”,40出头不仕不说,将妻子女儿撇在一边,一个月要拿出20多天伺候老母同睡一室,按理来说,海瑞不可能不在意海母的态度。 可事实上,海瑞的所作所为早已表明:不论海母是否同意,其赴任之心已决。 这种情况已经不合常理了。 而更不符合常理的却是:海瑞母子二人的一番对话。 深夜,海瑞按习惯拿着被来陪海母。 “知子莫若母”的海母看出了海瑞去意已决,便向海瑞了解起了内情—— 海母问信中的内容;海瑞先反问海母“田价”,随着海瑞的引导,当海母问道: “那为什么还要卖田,卖得这么贱?” 海瑞不经意间道出的话,十分可疑: “被逼的,官府还有那里的豪强,朝廷为了补亏空,要把浙江的田都改种桑苗,好多出丝绸、多卖钱。 “官府那些人和地方的丝绸大户,认准了这是个发财的机会,就要把百姓的田都买了去,还想贱买,他们串通了,趁着端午汛发大水把河堤毁了,淹了两个县,老百姓遭了灾,可他们呢不贷粮给他们度荒,就是想啊逼着百姓卖田活命。” 如果海瑞身处于现世,那这一番话无可厚非。 可今非昔比,海瑞所处的大明朝信息的传播远没有今日这般发达。即便有邸报这种专门发布朝廷动向与政策的东西,但可绝不可能把毁堤淹田、大户贱买田地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写上。 自然有一些事,朝廷里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,可身在边陲小县的一名教谕,还算不上是“朝廷中人”。 何谓“教谕”? 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,往大了说,可算“校长”,往小了说,就是一名教师。 在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中对“教谕”一职定义为: “儒学,府教授一人,训导四人。州,学正一人,训导三人。县,教谕一人,训导二人,教谕、学正、教谕,掌教诲所属生员,训导佐之。” 作为“教谕”,海瑞没有派系,更没有相应的“朋友圈”,从他嘴里说出的有些实情,连在翰林院做编修的高翰文都不太清楚,更何况海瑞呢? 在裕王面前,谭纶拿着张居正那字的信,对裕王说: “有了这封信,我料海公必出!” 由此可得,海瑞不太可能得到谭纶另外所写的信,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:海瑞一直用尽办法,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huanshegana.com/csgsltx/1549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天然食材大礼盒谁不想要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