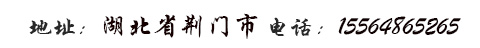强推鲁迅回忆录是难能可贵的佳作
|
今日推荐:《鲁迅回忆录》作者:许广平。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~ -----精选段落----- 五、所谓兄弟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,自己教书供给周作人在日本学习,那时周作人夫妇已经结婚,光凭一点公费,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,所以鲁迅在《自叙传略》上说:“终于,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,我便回到中国来,”这里“几个别的人”就是指周作人夫妇而言。周作人回国以后,鲁迅除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之外,连周作人老婆的全家,都要鲁迅接济。从日记上看到,鲁迅在每月发薪以后,就按月向东京羽太家寄款。这还不算,羽太儿子重久的不时需索和他的三次来到中国,鲁迅都有专款资助,甚至羽太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,也都是由鲁迅每月另行汇去的。后来鲁迅回忆起来说:“周作人的这样做,是经过考虑的,他曾经和信子吵过,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。他曾经说:‘要天天创造新生活,则只好权其轻重,牺牲与长兄友好,换取家庭安静。’”在搬出八道湾以后,鲁迅曾经这样说:“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,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,比较不那么发愁了。”对照以往生活紧张的情况,在搬出八道湾以后,则可以量入为出,并且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迫要求,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吧!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,和鲁迅却绝然相反。据说当他知道徐坤的劣迹以后,曾经这样表示:如果换掉徐坤,要他自己去办理一些身边琐事(如自己做衣服之类),太觉得麻烦了;要减少许多看书时间,而且自己也办不到,划不来,所以也就随他去了。这是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爷脾气: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四体不勤,好逸恶劳。这样说是不是冤枉了他呢?一点也不冤枉。有事实为证:人们只要翻开《鲁迅日记》,就可以看到鲁迅在年为了全家移居北京,就到处奔走另找房子,在多次看屋以后,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。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,办理手续。鲁迅又兼监修,又得向警署接洽,议价、收契,家具的购置、水管装置等等事务,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,房价不足,又四处奔走告贷,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(大约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千余元之外,全部费用约四千元之谱)。那末,这一时期,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?原来他在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假,和老婆孩子们全家到日本游玩去了,中间曾经一个人回来过一次北京,但过不几天又返回日本了。直至新屋成交之前,鲁迅先另行租了几间房子(因为新屋修理尚未竣工),新居粉刷好了,周作人带着他的家属和其妻舅重久一批人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北京。若说周作人对新屋落成没有费一点神思,那也冤枉了他,他在这方面确曾做过两件事情,一件是他在新屋修理将近完工的时候,曾经和他的家属、妻舅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后,像地主老爷似的顺道看了一次他的庄园——八道湾;另一件是他去了警局一趟,领回了房契一张。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新居数得出来的两件大功! 说到房契,这里还有一段故事。鲁迅不自私,原来立房契的时候,不写自己的名字,而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,倒是经过教育部一位同事的劝说,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。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,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浪用,但被鲁迅坚持不肯,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,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。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,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。等到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,这时周作人又故态复萌,要把八道湾的房子再卖出去了。风声传到鲁迅耳里,鲁迅为了阻止周作人这个行动,利用他爱财独占的弱点,曾经表示:“卖掉是可以的,不过也得要分我一份。”就因为这个缘故,八道湾的房屋才没有被卖出去。这时鲁迅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意见,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卖掉的了。因此这事才被搁置了二十多年。待鲁迅逝世,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以后,周作人做了汉奸,烜赫一时,他就私自把房契换成他自己的名字,算是他的,以便为所欲为。 在这里,我要提一提周作人的老婆信子其人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。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,初期每月工资不欠。不够时,就由他向朋友告贷。这样的人,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人手,这时,当然是要得的。后来,由于欠薪,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,那就妨碍了这个奴隶主的权威,“讨厌起来了”。于是便开始排挤鲁迅。她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,《呐喊》中《鸭的喜剧》里不是谈到爱罗先珂先生对鸭的喜欢吗?从母亲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,爱罗先珂来中国以后,就住在八道湾家里,和她们家人也熟识了以后,他又懂得日语,谈话没有什么不便,于是有时也就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劳动,“也屡次对仲密(周作人笔名——作者)夫人劝告,劝伊养蜂,养鸡,养猪,养牛,养骆驼。”也就类似现在所说的搞副业吧。“有一天的上午,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,咻咻的叫着;”“于是又不能不买了,一共买了四个,每个八十文。”这就养起鸭来了。喂小鸭的光荣任务,首先要找饲料,南方是容易得到的,田边上的小虫,鸭自己就会去寻食。至于在北京家内的水池,什么也不易得到,那就要烦劳徐坤去找。那徐坤却不费事,用高价买来了泥鳅喂鸭(在北京泥鳅较少,故价昂贵),算起来,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的钱还要多,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。在爱罗先珂先生,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,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过生活,话尚未完,信子已经怒不可遏,听不入耳,溜之大吉了。而言者因为看不见,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。她对朋友尚如此地不礼貌,对家中人自然更要凶悍得多了。据鲁迅说,她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,住在绍兴,那里没有领事馆,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,撒起泼来,顶多只是装死晕倒,没有别的花招。但有一回,这一花招却被她兄弟重久在旁看见了,就说不要理她,她自己会起来的。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。但到北京以后,她却不同了,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,北京又有日本使馆,她便倚势凌人,越发厉害,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。事事请教日本人,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。鲁迅被赶走后,一有什么风声鹤唳,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,改周宅为羽太寓,这也是周作人的奴性十足的表示,信子们唯恐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侵略中国,日本人来了,对她们很有好处。从这情节看来,鲁迅的痛恨卖国与周作人后来的甘心投日,即其本人的日常接触上,亦各自分野,截然不同的了。 唐弢同志编的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中,从周作人的日记里抄录了年2月鲁迅题为《别诸弟》的三首旧诗,充分表达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对兄弟的友爱,其中有这样一首: 春风容易送韶年,一棹烟波夜驶船。 何事脊令偏傲我,时随帆影过长天! 在诗的后面并有跋言云:“嗟乎,登楼陨涕,英雄未必忘家;执手消魂,兄弟竟居异地!”印证以后来鲁迅初到北京期间,和周作人通讯的频繁(据《鲁迅日记》,来往书信都有编号,前后各有三百封左右),邮寄书刊的不间断,人间友爱,兄弟之情,怡怡然异乎寻常。鲁迅曾经这样说:“让别人过得舒服些,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,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!”真是做到了“象忧亦忧,象喜亦喜”的地步。 然而风雨终于来临了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:年7月3日,还“与二弟至东安市场”等处,但到7月14日,却是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,自具一肴,此可记也”。紧接着7月19日,就是“启孟自持信来,后邀欲问之,不至”,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信,是什么样子呢?在信封外面写着“鲁迅先生”,在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“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!”兄弟的友情终于中断了,家庭终于决裂了。就这样,鲁迅在横逆忽来的情况之下,带着疾病,到8月2日,便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。这期间,鲁迅又带病到处看屋,另找住处,这样到9月24日,鲁迅大病起来了。当天日记记载:“咳嗽,似中寒”,第二天日记,又是“夜服药三粒取汗”,到10月1日,则是“大发热,以阿思匹林取汗,又泻四次”,10月4日,“晚始食米汁、鱼汤”,这样一直到11月8日,才“始废粥进饭,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”。 就是生着这样的重病,鲁迅并没有放弃工作。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,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,后来病倒在八道湾,也不给医治,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,病好才回去。周作人家有厨子,大批工人,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。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,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,在非常不安之下,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,在朋友援助下,终于在年10月30日另行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。翻修以后,于年5月25日移住新居。到6月11日,也就是离开八道湾将近一年之后,鲁迅回去搬自己的未搬走的书籍什物。八道湾的老爷和太太们,对于鲁迅本来是要像挤牛乳似地来榨取的,但他们没有想到鲁迅不向他们屈服,不但远离了他们,并且又安置了新居,于是就悔恨交集,多方刁难。当天的《鲁迅日记》这样记载: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huanshegana.com/csgsltx/1514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归来莫泊桑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